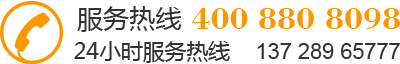唱片业“收入分配改革”
著作权法修改背后的版权分账博弈,谁是既得利益者?
“在一次人大会议上,有个代表指着我骂:‘你要脸吗?你怎么老要钱,怎么不学雷锋?!”词曲作家谷建芬说出这段话时,全场静默。
4月11日,这位77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中国现代流行音乐拓荒者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新闻通气会上说,“我们对版权的认知度太可怕了”。
当天,包括刘欢、小柯在内的众多音乐人现身这场由中国流行音乐学会唱片工业委员会(下称“唱工委”)组织的讨论会,主题是《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下称“草案”)。一如其他一些领域的立法,草案的部分条款以数字的形式出现成为争议代号,例如“第46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作品。
音乐人由此发出悲壮呐喊,直指版权收入分配不公。
“如果草案被通过,将对本来就岌岌可危的中国音乐产业的创新和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关系到音乐行业的生死存亡。”音乐人宋柯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这是一场围绕于音乐人、唱片公司和行业协会的博弈,谁是既得利益者?
谁是弱势群体
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就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4月30日。根据国务院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著作权法》修订从三档(需要积极研究论证的项目)提升为二档(需要抓紧工作、适时提出的项目)。
一时间,草案部分条款引来颇多争议,除了“46条”外,还包括“70条”——使用者依照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的合同或法律规定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报酬的,对权利人就同一权利和同一使用方式提起诉讼,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停止使用,并按照相应的集体管理使用费标准支付报酬。
谈及“46条”,鸟人艺术总裁、CEO周亚平认为,这相当于给别人做嫁衣。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下称“音著协”)副总干事刘平则告诉本报记者,草案条款内容是可以商榷的,若针对“46条”,其目的是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
另有业内人士表示,音乐人对“46条”完全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误读,其本身是对权益人的保护,一些国家连一天的保护期都没有。
音著协此前已表示,“46条”应与“48条”相结合来看,后者指出,他人使用著作权人作品须向版权部门申请备案,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作品出处,还要在使用后一个月内支付使用费,这一做法目的是鼓励传播。
耐人寻味的是,在上述唱工委通气会之后,音著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在4月13日公开表示,正式更改已提交的“修法意见”,要求删除草案第46条及48条。
“协会注意到自身在《著作权法》修法过程中存在的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书卷气以及对著作权人切身利益感受体验不深的问题。”音著协称。
目前,中国有两家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除了音著协外还有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
音著协年报显示,2010年总收益达到6801.86万元历史新高,参与版税分配金额为人民币3963万元。
截至当年年底,该协会会员总数为6154个,也就是说分摊到每人头上的版税收入为1万多元。这远不及一些音乐人的一次出场费。
宋柯表示,他见过有一首歌分过几毛、几元的,几百元相对多点。
业内人士表示,一首歌从创作到录制和推广,成长周期最少需要6个月,此后所带来的商业收益分两块,包括传播市场和演出市场。
“如果以草案46条实施的话,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48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这样,谁还会推音乐?脑子进水吗?”周亚平对本报记者说。
作为《两只蝴蝶》版权拥有方,周亚平说,如果“46条”出炉,唱片公司不会每月花6万为庞龙在各大音乐电台打广告,也不会在全国各地连线宣传,因为花这样的精力,推出来的将是无数个“庞龙”来瓜分原本只属于原创与唱片公司的一年2000万元的演出市场。
音著协此前也曾提及“46条”的不足之处——没有明确对著作权人报酬权的确保机制。
对于“46条”、“48条”,诸多音乐人认为是可以商榷的,比如,把3个月修改为3年,后面增加“著作权人声明不需使用的不得使用”的限定条件。
版权收益去哪了
音乐人担忧的不只是“46条”。草案“60条”称,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取得权利人授权并能在代表权利人利益的,可以申请代表后者行使著作权或相关权,权利人书面声明不得集体管理的除外;“70条”的明确范围则是,使用者依照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的合同或法律规定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报酬的,对权利人就同一权利和同一使用方式提起诉讼,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停止使用,并按照相应的集体管理使用费标准支付报酬。”
“这是两头堵啊!”周亚平说。
业内人士分析,在“60条”里,著作权人被集管组织给“代表”了,如果著作权人没有被集体管理而要维权,只要“侵权人”与集管组织签署过合同或者支付过费用,依据“70条”侵权人就不承担赔偿责任。
刘欢、小柯等音乐人即直言,这背后是商业利益的驱动,“草案出台的时候,代表各方利益的人都有,就是没有代表著作权人的。”
业内数据显示,目前音乐版权方每年拿到的收益不到10亿元,相当于整个产业产值的2%左右。
日本和韩国的版权方在数字音乐产业拿的分账比例是90%,在欧美,版权方拿到的平均产值是70%。
周亚平曾参与《两只蝴蝶》的无线市场开拓与CD销售,从中获得了几千万元的收益,但除此之外的权益却很难收到,2006年,周亚平曾为此打官司,后得知适用方已与一集体管理组织签署了授权协议,当时,周亚平并未与该协会签署协议入会。
不过,该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协会的账单每一笔都值得推敲,公开透明就差个人隐私没公布了,“我们的管理费只收取15%,这应是一个平均的数字。”
有音乐人建议,音乐版权机构应至少有三家,如果“60条”、“70条”不删的话,一些机构的圈地发展必将形成集体管理组织对音乐版权收益的垄断。
一些音乐人表示,目前音乐版权真正的收益方之一是北京天合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天合”)。
5年前,卡拉OK版权收费在各地陆续启动,当时同样引发争议。北京天合是中国音像协会和文化部委托的收费机构之一。
本报记者查询工商资料发现,这家正是成立于5年前,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出资单位分别为北京中文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华融盛世投资有限公司,各占股50%,目前已经在多个省份成立了“天合”公司。
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天合近年来均处于赔本赚吆喝的状态,2007年~2010年的净利润分别为-0.2万元、-879万元、-5969932元和-9266438元。
![]()